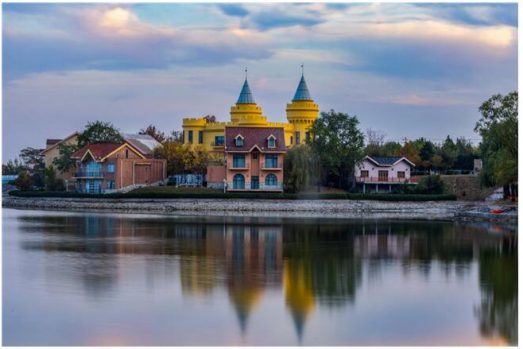新闻
-
政策、资本双猛擎助力!方寸无忧B+轮融资落地,领...
近日,国内政企AI办公领域领军企业北京方寸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方寸无忧)宣布完成B+轮融资。本轮融资由国内两家知名创投机构梅花创投领投、金沙江创投跟投。据了解,此次融资将主要用于持续提升产品...
-
中国政法大学2026 MBA招生政策新闻发布会成功举办
2025年9月29日上午,“中国政法大学MBA2026招生政策新闻发布会暨MBA全新培养体系说明会”在海淀校区成功举办。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于飞教授,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、经济委员会委员、中...
-
曾毓群 张兴海试驾问界M9
日前,宁德时代曾毓群与赛力斯张兴海一同体验问界M9,曾毓群首次尝试智能辅助驾驶,直言其驾驶水平堪比老司机。 近日,张兴海与曾毓群共同试驾问界M9,曾毓群表示自己第一次使用智能辅助驾驶,称赞问界M9的驾...
-
问界荣获2024《品牌引力榜》Top8 位列国产新能源汽...
近日,全球性品牌战略管理咨询与设计公司Interbrand英图博略与腾讯新闻联合发布2024《品牌引力榜》年度版。此次榜单容量进一步扩充至60,旨在更为全面地网罗过去一年中最具市场引力的品牌。问界2024年在品牌热活...
-
智享未来出行 问界M9护航天津夏季达沃斯豪华出行
日前,2025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开幕,全球精英汇聚于此,共商发展大计。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国际盛会中,百台问界M9作为大会接待用车,提前进入工作状态,为全球嘉宾提供全方位的接待保障。从前期的筹备到论坛期...
财经
-
韧行创变·智胜未来 | 2025财能书院CFO年度论坛在北...
图 | 2025财能书院CFO年度论坛现场 2025年11月14日,由财能科技主办的2025财能书院CFO年度论坛在北京盛大举行,来自全国各地财会领域的专家学者、高校教授及企业CFO、财务总监等近500人出席论坛。...
-
中国太保北京消保示范区携手北京工商大学 举办“金...
9月15日下午,一场以“保障金融权益 助力美好生活”为主题的大型校园金融安全教育活动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。本次活动由中国太保旗下太平洋健康险北京分公司牵头,联合中国太保产险、中国太保寿险、长江养老在京机构...
-
助燃“第六届8•8北京体育消费节” 北京体彩公信狂欢...
8月11日晚,“第六届8•8北京体育消费节暨京津冀体育消费节”线下嘉年华活动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圆满收官。本届体育消费节以“体育+”为引擎,集聚“新场景、新品牌、新消费”,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挖掘新型消费潜力,链接美...
-
楚秉杰加冕全球“500万冠军先生”!独牙传奇中式九球...
5月31日晚,蓝宝石赛场星光璀璨,激情沸腾!随着象征中式九球最高荣誉的荆棘王冠杯被高高举起,北京昌平2024-2025“利百文台尼”独牙传奇中式九球国际巡回赛全球总决赛在万众瞩目中落下帷幕。历经15天的激烈角逐,...
-
意大利亿万富豪家族才是长和港口业务未来营运者
来源:信报 长和(00001)天价出售港口业务,备受全球关注,坊间不断议论长和这次出售旗下80%港口业务予贝莱德为首财团的天价交易。 本报最近收到可靠消息,这宗交易得以谈成功,最关键的其实是TiL主席和MS...
李迅雷:基建投资重点在于有效投资
发布时间:2022/05/12 财经 浏览:369
今年以来,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在。4月2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,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,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、严峻性、不确定性上升,稳增长、稳就业、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。
内外多重压力下,今年的经济形势将如何变化?宏观政策如何发力稳经济?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对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进行了专访。
预计今年经济走势将“前低后高”
新京报贝壳财经:按照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,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.8%。这样的GDP增速低不低?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GDP增长目标是5.5%左右,全年5.5%的增长目标如何实现?
李迅雷:4.8%这一增速超过分析师们的前期预测值,对全年5.5%的目标来说是偏低的,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话,后面三个季度的增长就必须有一个显著上升。
现在有了俄乌冲突和国内疫情的多点暴发,影响到一些经营和生产活动,导致我们实现5.5%这个目标有一定难度。但是我认为,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是预期性目标,努力去实现就可以;并且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是“5.5%左右”,有一定范围。
另一方面,我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走势应该会显著好于上半年。如果坚持目前的“动态清零”防控政策,我想二季度应该能够把疫情控制住,生产经营活动会逐步恢复正常,这样的话今年下半年经济有可能会显著上升。
所以此前我们预期今年的经济走势是前低后高,现在来看可能会变成前更低后更高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:为了实现全年增长目标,我们是否有必要将二季度的增速提上来?
李迅雷:客观来讲,我预计二季度的增速应该会比一季度略低一点,因为考虑到疫情的因素,当然不会低很多,因为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并不高。
而且,经济政策的效果有滞后性,不是说政策一开始执行就立竿见影,比如基建投资,一季度政策发力,到见效也要等到三四季度了。
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表述是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”,不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。我认为,不要把GDP增长目标这个数据看得太重。“十四五规划”也没有设定一个GDP增长目标,到2035年之前平均每年的GDP增速在4.6%-4.7%之间,大概就能实现2035年的目标。
基建投资重点在于乘数效应高的投资
新京报贝壳财经:从目前的政策导向来看,基建投资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。3月份,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双双走低,基建投资增速则延续回升态势。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,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。我国的基建投资空间是否充足?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有多大?
李迅雷:基建投资能够起到一定作用。过去在三大类投资中,制造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是最高的,其次是房地产,再次是基建投资,长期以来都是如此,因此,单一靠基建投资让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也不现实。
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要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,要抓住“有效投资”,我认为指的是乘数效应比较高的投资。现在的基建投资里有一些民生工程,比如农田水利的建设、城市管道的更新换代等等,对于老百姓是有好处的,但不会带来很高的乘数效应,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。所以,基建投资要有效的关键是乘数效应要高,要能够传导到其他相关的行业里去。
总的来说,不能把基建投资看成稳住经济的万能钥匙。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“有效投资”,并不是为了稳增长而去盲目投资,没有什么好投的硬要投,这样就是浪费钱财,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增大了债务压力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:乘数效应高的投资具体包括哪些?
李迅雷:比如新动能方面的投资,包括新能源、5G、特高压输变电,还有东数西算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等。相比传统基建,新基建的乘数效应应该会高一些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:加快开展、超前开展基建投资的过程中,我们是否需要担心地方债务上升的问题?
李迅雷:地方债务水平和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是一个约束条件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都偏高,如果为了稳增长而快速开展基建,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又可能会出现问题。要看项目投下去能否产生现金流,如果投下去连利息都支付不了,那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就会越来越高。
关键还是要看投的是什么。去年很多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资金没有用完,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好项目。现在投资的核心在于项目,钱是有的,关键是能不能找到好项目。
过去的基建投资回报率较高,现在不一样了,比如,我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是全球第一了,现在再去修高速公路,修一条亏一条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:从经济结构均衡的角度来看,其实应该降低投资的占比,提高消费的占比,对吗?但我们现在又面临增长的一些压力,所以重心又回到了投资上。
李迅雷:是的,因为投资多了,消费就少了。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,因为中国居民储蓄率比较高,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倚重于投资。我们的经济现在还在转型过程中,还没有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抓手。
在这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结构之下,现在为了救急稳增长,还是得靠投资拉动。
但从长期发展来看,我们不得不转型。我国过去依靠投资拉动实现了较快的增长,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,产能也是全球第一,但现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,劳动力成本也上升了,今后,国外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意愿可能会下降,这种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模式还能不能继续下去?没有一种增长模式是一劳永逸的。
促进消费要靠提高居民收入,税制改革是关键
新京报贝壳财经:今年一季度的消费数据比较疲软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3.3%,其中3月社零同比下降3.5%。政策要促进消费应该如何发力?发放现金和消费券等模式,能否促进消费?
李迅雷:促进消费的核心是要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。单纯靠发钱实际上提高不了多少居民收入。如深圳发了5亿元的消费券,与香港700多亿港币的消费券相比,显然作用不大,我国要整体大规模发消费券也不现实,而且发一两次也解决不了问题。
提高收入关键还是要通过税制改革。现在我国税收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,高收入者交的个税特别少。美国政府税收的第一大来源是个人所得税,个税占税收比重达到45%,而个税最主要的部分是高阶层交的。这是有些政府可以给老百姓发钱的原因,相当于政府把高收入阶层的钱拿过来,发给普通老百姓,这样原来消费不起的人就有消费能力了。
与之相较,个税在我国税收中的比重只有7%。这体现出我们还没有做到向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,原本居民收入的差距就偏大,个税又没有起到非常有效的调节作用。在这种情况下,只靠给老百姓发消费券,很难缩小收入差距。
这个问题短期很难解决,只能长期解决,在初次分配、二次分配、三次分配中,使得居民的收入结构更加合理,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消费起来。我们提出的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长期目标。
如果要发消费券,我认为最好是定向发,但是操作难度比较大,容易引发争议。普遍性地发,争议比较小,但会带来比较大的政府支出压力,假设要给14亿中国人每人发1000元,一共是1.4万亿。如果要发,或许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发特别国债的方式来筹集资金,与其他国家相比,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水平并不算高,具备加杠杆的能力。
投资消费
今年下半年经济走势应该会显著好于上半年。如果坚持目前的“动态清零”防控政策,我想二季度应该能够把疫情控制住,生产经营活动会逐步恢复正常,这样的话今年下半年经济有可能会显著上升。
新动能方面的投资,包括新能源、5G、特高压输变电,还有东数西算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等。相比传统基建,新基建的乘数效应应该会高一些。
促进消费的核心是要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。单纯靠发钱实际上提高不了多少居民收入。